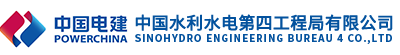將幸福注入國之重器 |
|
|
|
|
凌晨六點,桂南丘陵的輪廓仍隱沒在墨色之中,靈東泵站的板房已亮起第一盞燈光。工區長李不哈四郎推門而出,山風瞬間灌滿他的工裝。他深吸一口氣,風中夾雜著泥土的腥澀與龍眼樹的清苦,這是水利人最熟悉的“開工味”。 D1標段是這龐大水網的“咽喉”。圖紙上那些冷靜的紅色線條,意味著要劈開山嶺、鉆透巖層,讓清流穿越亙古的阻隔,去滋潤遠方焦渴的田疇與城鄉。但首先,他們必須成為大地的“讀心人”。 李不哈四郎領著年輕的施工員小孫站在工地上,指著腳下的土地語重心長地說:“我們千辛萬苦來到這里,就是為了這個工程。”他頓了頓,目光深邃地望向遠方,“你現在腳下踩著的這片看似普通的土地,等到明年這個時候,在地下幾十米的深處,將會有湍急的水流奔涌而過,每秒的流量能達到兩三個立方米。”說著,他轉向小孫,語氣中帶著幾分激動,“這些清澈的水流會沿著我們修建的管道一路向北,最終流進千家萬戶。想象一下,當這些水流到你家鄉,你父母打開廚房的水龍頭,用這些水淘米洗菜、煮飯燒湯時,作為參與這項工程的建設者,你心里會是什么感受?那種成就感和自豪感,是用金錢無法衡量的。” 小孫愣住了,他第一次不再將自己視為一個疲憊的施工員,而是想象自己成了那無形之水的一部分,一道即將誕生的奔流。那一刻,他臉上的疲憊被一種悄然降臨的鄭重感取代。 真正的挑戰在于羅陽山隧洞的開挖工作。地質條件的復雜性遠遠超出預期,羅陽山作為滑坡形成的山脈,地下全為松軟的土層,破碎的巖層不斷涌水,導致工程進度一度嚴重滯后。在生產周例會上,項目經理周成賢堅定而果決地說道:“山體不會主動為我們讓路,那就憑借技術和毅力,一寸一寸地艱難推進!” 于是,技術攻堅組的燈光徹夜不熄;老師傅憑著幾十年經驗,提出調整支護方案的建議被迅速采納;年輕的技術員們日夜守在電腦前,反復模擬著不同工況下的施工參數;大家圍坐在一起,熱烈討論著每一個可能影響工程進度和安全的細節,不斷優化著施工流程;工人們主動放棄休息時間,加班加點地施工,用汗水和堅持一點點突破著地質的阻礙。 同時,泵站提水線路的鋼管段也讓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。這段總長3.2公里的地上“動脈”,作為連接水源與干線的關鍵環節,必須在汛期前實現貫通。 “汛期不等人!”這句話已成為項目部的口頭禪。倒計時牌上的數字每日更新,宛如擂響的戰鼓。焊接工老田在狹窄的管廊內一待就是十幾個小時。質檢員趙乾手持手電和檢測儀,對每一道焊口進行細致的“體檢”,絕不放過任何毫米級的偏差。 當巨大的鋼管被吊裝設備緩緩放下,精準地嵌入預定位置時,焊工們立即上前作業,藍色的焊弧如節日焰火般綻放。當最后一道焊口完成,不知誰率先鼓起掌來,頃刻間,掌聲、歡呼聲、吶喊聲響成一片。 “提水線路鋼管段貫通了!我們貫通了!”人們激動地相擁而泣。較原計劃提前整整半個月,他們成功搶在了汛期到來之前。 所有人都再次歡呼,歡笑聲在管廊里久久回蕩。這不僅是“為者必成”信念的體現,更是水利人獨有的、提前品嘗到的“幸福水”那甘洌滋味的真實寫照。 我忽然明白了水利人的幸福究竟是什么。它不總在通水典禮的聚光燈下,更深藏于這開拓的艱辛之中。它是施工員腳下從無到有的第一條路;是技術員圖紙上穿越山河的紅色弧線;是爆破工在巨響后看到的完美斷面;是澆筑工抹平的最后一寸光滑混凝土;是提前半個月貫通的鋼管里,已經可以想象出的汩汩水流。 他們的幸福,是創造的幸福。他們將青春與汗水作為砝碼,押注于一個關于未來的清澈誓言。于是,個人渺小的生命,便通過這條地下的動脈,與千萬人的生計冷暖、與一片土地的繁榮重生,產生了永恒的聯系。 幸福如水,水利人的幸福,是水之將至時,那澎湃于心的潮聲。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