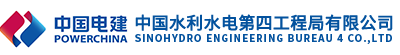工地上的“大嗓門”和“婆婆嘴” |
|
|
|
|
孟底溝水電站的工地,是一個由鋼筋、混凝土和人類意志構成的世界。無人機與機械轟鳴交織在一起,載重卡車的引擎如同巨人的喘息。在這里,有兩種聲音,超越了一切喧囂,成為工地上最鮮明、最動人的標識——它們是生產調度員嘶啞的吶喊,與安全員永不疲倦的嘮叨。 對講機里吼出的施工進度 生產調度室,是工地的“中樞神經”。對講機的電流聲、電話鈴聲、人的喊叫聲,在這里混響成一曲緊張的交響樂。 生產主任何玉倉,正對著對講機咆哮,他的嗓子像一面破鑼,卻有著穿透一切的力量:“喂!喂!老李!混凝土罐車到了哪點了?啥?堵車了?你跟老子說啥子哦!想辦法,十分鐘內必須給我疏通!” 剛放下手機,立刻又抓起報話機:“李隊長!你自卸車呢?說的10輛車,現在只有5輛是干啥呢,下午三點前必須到位!” 作為生產辦主任,他每天的工作就從這一聲聲急促又有力的呼喊開始。孟底溝水電站建設規模大、工期緊、涉及環節多,從設備調配到人員安排,從施工進度把控到突發問題解決,每一項工作都離不開他的統籌協調。為了確保各項任務按時推進,他每天穿梭在各個施工區域,遇到問題第一時間溝通解決,而“喊”則成了他最高效的工作方式。 “何主任嗓門也太大了,有時候隔著半個工地都能聽見他喊。”新來的大學生們私下里會嘀咕。可小調度員韓亞洲卻知道,那嗓門里藏著多少不得已。他剛到工地時,就因為說話像蚊子哼,被何玉倉狠狠“吼”過一次。 那是每周一次的施工協調會,會議室里坐滿了各個施工隊的老板,一個個煙癮大的,把屋里熏得像個煙囪。韓亞洲負責匯報上周各隊伍的施工進度,手里攥著寫得密密麻麻的報表,手心全是汗。一開口,聲音就發飄,越說越小,到最后,后排幾個年紀大的施工隊老板干脆掏出手機看。 散會時,何玉倉把韓亞洲叫到辦公室,順手扔給他一瓶冰鎮礦泉水。“聲音為什么那么小?”他沒發火,只是盯著韓亞洲的眼睛,“你穿的是項目部的工作服,坐的是調度員的位置,你說話沒底氣,別人怎么信你?那些施工隊老板都是老江湖,你聲音小一分,他們就敢跟你打十分的折扣,到時候進度拖了,誰來擔責任?” 韓亞洲低著頭,聽見何玉倉又說:“我剛上工地的時候,比你還不如,說話臉紅到脖子根。我師父天天在我耳邊吼,吼得我后來見了問題就敢喊,見了推諉就敢頂。工地上的嗓門,不是喊給別人聽的,是喊給自己的責任心聽的。” 后來韓亞洲才知道,何玉倉的師父,是工地上一位老調度員。那老調度員,一輩子都扎根在這工地,對每一處施工細節都了如指掌。他平日里話不多,可一旦到了工作上,那嗓門一扯開,整個工地都能聽見。他用自己的方式,教會了何玉倉如何在工地上立足,如何用那響亮的聲音,扛起責任的重擔。 原來這“破鑼嗓子”,早就是調度員之間的一種傳承——用最直接的呼喊,扛起最沉重的責任。 安全帽下嘮叨來的平安歸途 如果說調度室是工地的“中樞神經”,那安全員就是守護生命的“免疫系統”。安環部主任劉世明,就是這個系統里最較真的“總司令”。他個子不高,皮膚被高原的太陽曬得像塊深褐色的巖石,走起路來腳底板帶風,手里總攥著個黃色的安全巡查本,而那張嘴,更是像臺上了發條的復讀機,從早到晚,嘮叨個不停。 “師傅!安全帽帽帶!”一大早,劉世明就盯上了正在綁扎鋼筋的老張。他快步走過去,伸手把老張頭上歪掉的安全帽扶正,手指扣住帽帶用力一拉,“跟你說了八百遍了,要系緊!不是把帽子扣在腦殼上就完事了!你這腦袋要是被鋼筋砸一下,帽帶松了,跟沒戴有啥區別?” 老張嘿嘿笑著,趕緊把帽帶系緊:“劉主任,知道了知道了,這不是著急干活嘛。” “著急也不能拿命開玩笑!”劉世明又瞪了他一眼,轉身就看見不遠處的腳手架上,一個年輕工人正單手抓著鋼管,另一只手去夠遠處的扳手。“那邊那個小伙子!你看啥子看,就是你!”他仰著脖子喊,聲音里帶著急,“高空作業,安全帶的雙鉤呢?說了多少次交替行進,你把規范當耳旁風?” 那工人嚇了一跳,趕緊把另一個安全鉤也掛在了鋼管上。工友們私下里都叫劉世明“劉婆婆”,覺得他太磨嘰,一點小事都要嘮叨半天。可劉世明不在乎,他走到哪,嘮叨就跟到哪,身后總跟著個年輕徒弟,叫朱書哲。 朱書哲剛從安全工程專業畢業,滿腦子都是“風險辨識”“應急預案”的理論,一開始對師傅的“碎碎念”特別不理解。他覺得安全檢查只要看數據、查記錄就行,沒必要揪著工人袖口沒扣、手套破了個洞這種小事不放。 直到有一次,他們巡查到鋼筋加工場。一臺鋼筋切斷機正在嗡嗡作響,老工人李師傅正彎腰往進料口送鋼筋,袖口的扣子沒扣,松散的布料隨著機器的振動晃來晃去。 朱書哲還沒反應過來,劉世明已經一個箭步沖了過去,伸手就抓住了李師傅的手。“老李,又是你!”劉世明的臉色沉了下來,他走過去,沒先批評,而是伸手幫李師傅把袖口捋好,一顆一顆扣上扣子,“跟你‘嘚啵嘚啵’多少回了?這袖口要是卷進去,機器轉速每分鐘上千轉,你這胳膊就算廢了!” 李師傅的臉一下子紅了,訕訕地說:“劉主任,我下次一定注意。” 走開后,劉世明看著一臉不以為然的朱書哲,突然停下腳步,問:“覺得我煩了?” 朱書哲沒敢吭聲,心中卻也覺得主任小題大做。 劉世明嘆了口氣,語氣緩和下來。“小朱,你覺得我一天到晚嘮嘮叨叨,討人嫌,是吧?”他頓了頓,聲音里帶著一絲疲憊,“可我上班這么多年,我是不希望有任何能阻止的事故發生在我眼前。” 他轉過頭,目光灼灼地看著朱書哲,眼里布滿了血絲——那是常年熬夜巡查、喊話喊出來的。“你看咱們這個工地,山高路險,夏天曬得能烤熟雞蛋,冬天風大得能吹跑安全帽,到處都是看不見的隱患。我每天轉來轉去,嘮嘮叨叨,不是沒事找事,是怕我漏了哪個角落,就有人要出事。等你啥時候能像我一樣,看到一點隱患就渾身不舒服,不嘮叨出來就睡不著覺,你就算出師了。” 朱書哲看著師傅黝黑臉上那無比認真的神情,心里猛地一震。他突然想起,前幾天暴雨過后,師傅凌晨兩點就起來巡查邊坡,生怕出現滑坡;想起師傅每次看到新工人,都會拉著他們講安全案例,講得口干舌燥;想起師傅的巡查本上,密密麻麻記著每一個隱患點的整改情況,每個月初都要走一遍工地各個角落,每個滅火器都要親自檢查。原來那些令人厭煩的“嘮叨”,每一句都藏著對生命的敬畏。 從那天起,朱書哲也開始學著“嘮叨”。他會蹲下來,跟綁扎鋼筋的工人說“扎絲頭要朝里,別劃破手”;會仰頭跟腳手架上的工人喊“腳下的踏板再檢查一遍”;也會不停地說著那句“安全帽帶拉拉緊”。他的聲音還帶著年輕人的青澀,卻也像師傅那樣,帶著不妥協的認真。漸漸地,工地上又多了一個“小婆婆嘴”,把這份守護,悄悄接了過來。 峽谷間交織成的豐碑答卷 在孟底溝,何玉倉和他的“大嗓門”團隊,與劉世明帶領的“嘮叨鬼”兵團,構成了工地生態的獨特兩極。一個在追求極限的效率,一個在守護絕對的底線。他們時而會因為“搶進度”和“保安全”爭得面紅耳赤,但在食堂遇到,又會坐在一起,互相遞上一根煙,吐槽著彼此的“不容易”。 他們的聲音,沒有機器轟鳴那么響亮,卻比鋼鐵更有溫度。何玉倉的吶喊里,藏著對工期的焦急,對工程質量的執著;劉世明的嘮叨里,裝著對工人的牽掛,對生命的守護。這兩種聲音,一個追著效率跑,一個守著底線走,看似矛盾,卻又缺一不可,像兩只手,緊緊攥著工程的安全與進度。 他們的聲音,是這片熱土上最平凡,也最偉大的聲音。它不似機器的轟鳴冰冷,它帶著人的體溫、情感與責任。這聲浪,裹挾著沙塵與汗水,升騰在峽谷之間,最終,將融入未來大壩蓄起的萬頃碧波,轉化為點亮千家萬戶的清潔電能。 那些喊過的話、嘮叨過的事,沒刻在紀念碑上,卻記在工人的心里——是何主任吼著疏通的堵車,讓混凝土沒耽誤澆筑;是劉主任念叨的帽帶,讓自己沒被掉落的工具砸到。或許某天大壩蓄水發電,工人們坐在家里看電視,會想起孟底溝的日子,想起那些曾讓他們嫌吵的聲音,然后笑著跟家人說:“當年工地上有個‘大嗓門’和‘婆婆嘴’,多虧了他們啊。” |
|
|
|
| 【打印】 【關閉】 |